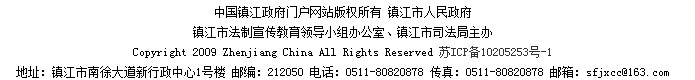□郝铁川
今年是英国《大宪章》问世八百年。由于英国《大宪章》具有鲜明的限制王权的思想,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它是人类第一部宪法文献。但若将其置于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就不难发现学界的评价失于过高。
1215年6月15日,英格兰的封建贵族聚集伦敦,挟持国王约翰,逼他签署《大宪章》。该契约共有63条,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第61条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二是第39条规定,未经同等级者的合法裁判,对任何自由人不得施行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放逐出境等处分。这两条构成了对王权的实质性限制。
然而,且不论别的国家,单看中国历史上限制王权的理论学说和法律规定,就要比《大宪章》早两千多年。
征诸目前的历史文献,至少在公元前11世纪的周朝就有了限制王权的规定,这主要体现于周朝的习惯法——周礼。根据周礼的习惯法规定,一方面,君主依据周礼对贵族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另一方面,贵族对君主亦拥有谏、逐、诛等合法的权利。
谏,就是批评。《尚书大传》说:“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弼天子之过也。”《周礼》于地官司徒下设“保氏”,专门“掌谏王恶”。《国语·周语上》记召公语云:“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君如果拒谏弭谤,就有可能受到“放”或“诛”的处分。
放,即流放。如西周厉王被公卿大夫流放于彘。春秋时期被放逐的有过之君更多。《春秋》记载此事所用的表述方式是:不言逐而言奔,且多书出奔者名。昭公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晋代杜预注:“不书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其他如:郑伯突出奔蔡(桓公十五年);卫侯朔出奔齐(桓公十六年);卫侯出奔楚(僖公二十八年);卫侯出奔齐(襄公十六年);蔡侯朱出奔楚(昭公二十一年);莒子庚舆来奔(昭公二十三年);邾子益来奔(哀公十年)。
放逐国君,时人无有非议。如毛公鼎铭文载,宣王即位,对其父厉王暴虐罪行直言不讳,对放逐厉王的臣民无有不满之意。春秋时期的王子朝更径言“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左传》昭二十六年)。
诛,即“弑君”。弑君事件中,有些纯属乱臣贼子的犯上行为,但确有一部分是因为君主无道而被人处死的。《春秋》记录此事所表达的方式是:如属国君无道而见弑,一般书君名而不书弑者名;弑者如为大臣则称其国名,弑者身份较低则称其为“人”。成公十八年:“晋弑其君洲蒲。”杜注:“不称臣,君无道。”襄公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杜注:“不称弑主名,君无道也。”其他如:莒弑其君庶其(文公十八年);吴弑其君僚(昭公二十七年);薛弑其君比(定公十三年);卫人杀州吁于濮(隐公四年);齐人弑其君商人(文公十八年);宋人弑其君杵臼(文公十六年)。
诛杀无道之君的理由在于“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若以邪临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专则不能使,至于殄灭而莫之恤也,将安用之?”(《国语,鲁语上》)
总之,君主对贵族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而贵族对君主亦拥有谏、诛、放之权利,是一种双向制约的关系。所以,一方面是“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左传》襄公十四年),另一方面又是“有君而为之贰……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左传》襄公十四年)。这两种看似并不一致的原则,在周礼那里却是并行不悖的。
秦汉以下,分封制被郡县制、贵族制被官僚制所取代,周礼作为习惯法也被成文法取代。但是,周朝贵族制约君权的习惯在秦汉以降的君臣关系中仍有保留。这主要表现为宰相对皇帝有两种制约权,一是不肯副署权,即:宰相如果认为皇帝的诏令不正确,可以拒绝副署。没有宰相副署,诏令没有法律效力。唐朝武则天下敕惩治刘祎之。刘祎之见敕文未经中书门下副署,遂说:“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名为敕?”二是奉还诏书。即:宰相如果觉得皇帝诏令不正确,可以退回皇帝三思。
正是因为周礼中有贵族限制君权的规定并且有此规定付诸实施的历史记载,继承周礼思想的儒家才有大量臣民可以约束王权的论述。最典型的是《孟子》所载:“齐宣王问:‘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粱惠王下》);“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乎变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在孟子看来,国王的宗亲贵族可以革除无道之君;异姓贵族则可以批评国王,国王不听就离他而去。
另一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不论是宗亲贵族、还是异姓贵族,对无道之君都拥有“谏、争、辅、拂”等权利:“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通“诤”);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通“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通“弼”)。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荀子·臣道》)荀子所言的“谏”是批评;“争”是以死进谏;“辅”是聚集群臣百官强行纠正君主的过错,类似“兵谏”;“拂”是指暂时代行君权,安定天下,类似“挟天子而令诸侯”。
因此,中国古代的周朝已有较为系统的限制王权的思想理论、法律规定和具体实践,比英国《大宪章》要早两千多年。限制王权的法律和理论源远流长,但我们能否循着这一轨迹追寻近代宪法政治之发轫呢?我认为恐怕不能。 近代宪法政治是由以下几个要件构成的:第一,产权多元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是近代宪法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没有市场主体的多元性,就不会有多元的政治力量,而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第二,宪法的实施必须以民主为基础。民主有多种形式,但核心是公民对国家重大事项的投票权。民主是保证宪法实施的前提。第三,社会具备普遍的人权、平等、自由等宪法意识。而近代以前的社会结构特点是: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富贵不分的贵族阶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维护君主、贵族等少数人利益为主的特权法。这样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产生近代宪法政治的。因此,过高评价英国《大宪章》是不符合注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根本观点的。
英国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氏这些论断当然具有唯意志论色彩,但他揭示了一些人发思古之幽情,恰恰是为了当代的真相。历史遗产非常丰富,从中汲取什么,是由人们的现实需要决定的。中国的依宪治国需要汲取什么样的历史资源,要由当今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求来决定。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