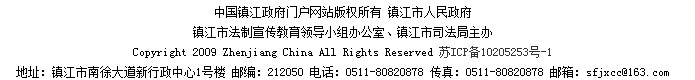彭宇案引发了什么问题
2007年9月4日,江苏省南京市某基层法院在彭宇案一审判决中错误地运用经验法则进行事实推定,宣示了一项被认为是“做好事没好报”的法则,在中国社会道德信仰危机的沉重背景下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二审法院又因社会的强烈质疑而以调解方式了结此案,回避了社会公众对于事实真相的强烈关注和对行为准则的热切期待。随后,媒体相继密集地报道了在全国各地上演的不同版本“彭宇案”……接踵而来的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一系列见死不救的报道。而在所有这类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链接或指向了南京彭宇案。
彭宇案审判的影响如此深远,不仅令当事人自己和本案法官始料不及,也着实让整个司法界“受宠若惊”!就新闻本身的特点来说,事件发生的概率越小越有新闻价值。但问题在于,公众不会因为一则人咬狗的新闻而相信这是一种常态,却为什么会因为一则彭宇案的新闻而坚信这种判决才代表中国司法评判社会道德的常规或惯例?如果这种意识或信条成为一种普遍认知,那么彭宇案判决运用的“经验”(法则)究竟是(已有)社会认知的反映或结果,还是导致(后来)这种社会意识的原因?
问题的答案背后,蕴藏着社会意识、公众信仰、价值取向等更深层次的命题,值得司法界、新闻界和社会公众共同反思。然而,最应该从彭宇类案中深刻反省的还是司法界本身——面对社会信仰危机,司法应具备怎样的角色或职能才能担当使命?面对公众对真相和正义的渴求,特别是面对媒体的监督或误导,司法应以奉行怎样的原则和规范从容应对?在信仰危机与价值重构的国度与时代,司法应有怎样的功能与特质,特别是在涉及社会行为规范的热点案件上司法与媒体应各自奉行怎样的准则、又应形成怎样的互动关系?“彭宇案现象”只是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透视窗口,本文的分析也只能择其要领、点到为止。
信仰缺失下的司法角色
信仰是人们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选择和倾向。在一个宗教信仰强大的国家,人们容易相信:即使法官偶尔瞎眼、上帝也不会睡着,恶行即使未受到俗世审判制裁、也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这种信仰一方面会加强行为人的自我约束,另一方面也为其他社会成员受伤的心灵提供平复机制。相反,在一个普遍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家,一方面行为人的内在约束机制很差,另一方面公平诉求的心理资源也很缺乏,因此更加依赖于司法这样外在的制约和正义诉求。中国社会基本没有宗教信仰,转型社会的价值紊乱也打碎了普遍的道德信仰。于是伸张正义的压力几乎全都压到了外部控制途径——司法正义诉求上。彭宇案判决异乎寻常的巨大轰动,正是这种在信仰危机背景下社会期待司法拯救信仰的愿望落空而引爆的。
然而,司法与信仰之间的互动与纠结绝非单向或单一维度的。通过司法等外部控制而产生的信仰,是一种可印证(或推翻)、可预测、具有外部威慑性的信念或信条,因而外部控制的形成也依赖于多重外部条件的满足。司法除了要有对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标准确定的裁判与惩罚之外,首先需要有强大的侦查能力或其他获悉事实的手段,足以发现事实真相。司法公正的重要指标就是法官认定的事实与原始事实最大程度的接近。然而,法官既非掌握事实真相的当事人也不在现场,相反却是最后接触证据的人。如果整个社会没有信仰,比如证人普遍不说真话、社会也普遍不信任法官自由心证,那么就只能借助于有形证据来确立事实,从而导致“事实=证据=书证+物证”的现状,不仅导致发现事实的成本高昂,甚至因不得不忽略本已影响法官心证的大量有效信息(如当事人陈述或证人作证时的举止异常、逻辑冲突等)从而无法合乎情理地发现真实;如果法官本身对于社会道德的整体状况缺乏信心而成其为一种“经验”性结论(信念),则可能出现彭宇案判决那样错误的“经验”推断;而基于这种经验而作出不能惩恶扬善的判决如果真的成为一种司法常态,则又进一步恶化社会的信仰。
新闻监督与公正审判的紧张与衡平
毋庸讳言,在“彭宇案现象”的形成、发展直至大有“丁蟹效应”似的“自我应验”趋势中,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众的代言人对于社会心理的形成扮演着推波助澜的重要角色,值得新闻界深刻反思和警惕,更是司法与媒体关系中值得重视的课题。
中国司法与传媒之间本能似地显现出某种不正常的紧张关系:媒体一旦关注,审判就发生扭曲。在彭宇案中,当彭宇在第二次庭审中陷于事实不利地位时,这位出身于网络媒体的小伙子在第三次庭审中引入了媒体监督。而一审法官则乱了方寸——在根据彭宇的自认、结合当班交警电子笔录、通过传讯交警和原告儿子等目击者当庭质证、适用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明标准,已经基本可以认定不利于彭宇的事实的情况下,却可能担心理由不够充分,画蛇添足地运用所谓“经验法则”、以“人性恶”的个人经验判断作为社会一般经验判断的事实推定。在一审判决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二审法院更是谨小慎微,在已经找到事发当日交警记录、完全可以确认两人相撞事实的情况下,却在二审即将开庭之际,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根据和解协议书的明确要求,赔偿责任和数额都不得公开。于是,彭宇案的事实真相直到今日也不是“公开审判”的结果。
那么,这种经不起媒体关注的审判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与此相关的“媒体审判”的现象又何以得逞?因为媒体及其代言的公众往往通过绑架权力机关而影响司法,因此这种影响力量并非来源于媒体关注本身,而源于媒体关注惊动的“有关领导”。媒体的标签化报道误导公众固然违反新闻伦理,但媒体报道直接影响到由训练有素的职业法官(而不是作为普通公众的陪审团)作出的司法结果。
长期以来,中国司法判决所承担的功能并不只是依据本案的事实和相关法律作出正义裁判,而是要兼顾和承担社会保障功能、作出符合社会效果的裁判。因此,司法往往试图在判决中兼顾公民之间的困难“救济”问题。在中国社会保障机制、社会保险机制不健全的情形下,司法对于事故责任的评判往往不只是考虑事实和过错,而是同时甚至重点考虑损失后果的分担,于是产生了大量在事实不清、过错不明的情况下适用“公平责任”。然而,这种不问事实、不论过错的“公平”责任,实际上当然并不公平,由此导致的深远后果就是使得跌倒老人以及社会上其他需要救助的人成了烫手的山芋,谁沾谁倒霉。以关注司法的“社会效果”建立起来的司法制度,却恰恰制造出越来越多负面社会效果的判决,因为没有是非就没有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和谐。
证据规则与证明责任体系的反思
在法律规则和技术层面上彭宇类案也提出了多重挑战,比如自由心证原则、证据规则中排除救助行为之自认效果的安全港规则、非机动车之间及其与行人之间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中的过错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分享)规则及其证明标准问题,等等,都是值得重申或重新思考的重大课题。此类案件的共同特征,都是存在事实查明困难。南京彭宇案违反伦理的“经验法则”,天津李云鹤案匪夷所思的“惊吓说”,都有在存在证明困难时,法官根据当事人双方的陈述和有限的证据,在内心里实际上已经就事实真相形成了倾向性判断(心证),并据此对实体结果的大致公平性产生了某种隐约甚或明晰的良知。但制度上并未赋予法官自由心证权,同时规定原告就过错责任的全部要件承担证明责任,并且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认定)标准。因此法官明白以目前掌握的证据并未满足认定事实的法定标准、无法适用相应法律以支持其内心和当事人对实体公平的诉求。此时再加上媒体和公众的压力,一些既缺乏外部独立也缺乏内部独立而且也缺乏审判经验的法官,就可能以为多拼凑理由就能增加事实的盖然性和理由的说服力,从而出现画蛇添足的现象。
在此应当重申一些已知的规则或常识:首先,作为裁判的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也不同于新闻事实。即使按照高度盖然性标准,法律事实也只要求达到“大致可能”(70%或75%)。但这一标准仍然明显高于新闻事实,因为法治国家为了保障新闻自由对于新闻事实都采取了较低标准,比如新闻报告只要不是无中生有、恶意中伤,就大致符合新闻事实的要求。这也导致公众从新闻中获取的事实可能与客观事实有较大出入,与司法程序最终认定的法律事实也大相径庭。而缺乏独立的法官一旦面对媒体、公众及有关领导的压力,便可能在潜意识中要求事实证明标准高于“大致可能”这一模糊标准,不敢理直气壮地按照这一证明标准公开心证、作出事实判断,而是从自己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证据规则中寻找和堆砌说服公众的理由,但这种画蛇添足却往往导致法官作出的事实认定既背离常识、又没有正确适用规则的情形。
其次,证据种类并不只是书证、物证,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都是重要证据,甚至在缺乏书证物证的情形下成为必须和主要依赖的证据。特别是在交通侵权案件中,获得物证和书证的概率较小,如果能够认真、细致、机智地调取、观察和判断亲历事件的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目击事实的证人的证言,查明事实、获取心证的概率要增加许多倍。
最后但最为重要的是,必须明确赋予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对事实作出综合判断的权力,同时应当在民事诉讼中建立明显区别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并可以考虑允许法官在侵权案件证明困难时降低证明标准。
在实体法领域,交通事故除了机动车辆采用特殊侵权责任规则并以保险责任加以补充和平衡,非机动车辆之间及其与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和相应侵权责任也应当有别于普通侵权责任,因为与普通侵权行为相比,这类行为仍属于风险较高的领域,而且往往主观过错较难证明,如果均由原告单方承担证明责任,则会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大大增加原告的证明困难和败诉风险,在具体案件中往往导致不公平的裁判结果。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在过错事实乃至行为及因果关系事实尚未查清的情况下即适用公平责任的案例,部分根源于这种不公平的证明责任分配在个案中的适用违背了法官内心的公平观和实体正义感。
一个缺乏信仰的转型中的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规则,需要法官有更多的独立判断和更多的信任资源。同样,媒体在形成健康的社会心理和塑造社会信仰方面也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形成健康共识,拯救社会信念,是司法的责任、媒体的责任,更是政治家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